作者:生活的阴暗面
2020年/5月/13日发表于第一会所
非首发
曾以同名ID首发于混沌心海
字数:6328
我叫陆萍,朋友们都叫我萍萍。
放眼这个偏僻小镇的百年历史,我或许是拿到博士学历的唯一一位女人。
「陆萍是混沌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女作家,也是一位命途多舛的女革
命者。她以女性的生命体验,洞察到以男性为主体的革命阵营内部,既有着两性
间在阶级、民族利益上的一致性,还存在着男性以革命的名义对女性的歧视。她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大胆而犀利地揭示出被革命外衣遮蔽的性别歧视问题,从而
挑战了革命群体内依然固有的父权- 夫权制性别秩序。」
能以年轻作家的身份进入文学史,确实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
今天,我回家了。
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心海镇。
心海镇对我来说是一片沼泽地,我陷入其中无力自拔,我总有一天会被心海
镇所淹没,这是我命定的悲剧。在这一天尚未到来之前,我要一次次地回到心海
镇的故事中。
这是另一位女人的故事。
这个女人又年轻又美丽,这样的女人很容易死于非命,使男人们惋惜,使丑
陋的女人暗暗庆幸。
这样的女人还往往是演员。
在混沌国,在本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前期,年轻漂亮的女人被收集
在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太祖思想文艺宣传队里,在工厂、矿山、学校、县城、公
社,漂亮的女人是宣传队的台柱子,她们扮演吴清华、李铁梅、白毛女、小常宝,
她们因此成为荣誉和诽谤的中心。
阮钰就这样被传奇化了。
阮钰在舞台上披着长长的白发,一身雪白飘动的绸衣,袖口和裤腿被剪成花
瓣凋零的形状。在转暗的灯光下,白色的阮钰幽灵般从台侧二道幕飞奔而出,如
一道惨白耀目的闪电照彻全场。阮钰在台中猝然站住亮相,像飞奔的瀑布突然凝
结成冰柱,惊雷一停,阮钰愤怒地唱道:「我是山上的大树——」
她黑色的眼睛闪出火光,火焰四溅,魔法般使全场观众屏息良久忘记世界。
「我是山上的大树——」
阮钰尖利的歌声像利剑寒冷地掠过剧场的屋顶,寒光闪闪,多年以后还深刻
地停留在我的耳膜上。
县文艺宣传队改演舞剧《白毛女》是几年以后的事,阮钰那时演的是歌剧
《白毛女》。直到现在,镇上的人们还认为,改演舞剧是因为少了阮钰这样的台
柱子。一个人又要能唱又要能演,还要长得漂亮,这是很难的,除了阮钰,再也
没有第二个了。现在离当时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心海镇文艺队的女演员换了无
数批,还是没有人能比得过阮钰。
阮钰是一个辉煌的时代。
阮钰在她死之前一直住在心海镇上,住在她舅舅家的阁楼里。她舅舅家的大
门又旧又脏,正对着大门的是一条非常瘦小却极长的过道,长得看不见头漆黑一
片,从街上往里看就跟看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差不多。阮钰从这么一条隧道里走
出来,更显得光彩夺目。
阮钰的舅舅是个从不说话的阴沉老头,整天坐在门口的骑楼底下用一根铁把
纹绳子。有一次我走近他看他怎么把绳子做出,他的老婆斜靠在门框上打线衣,
她一边打一边拆一只白纱手套。老阮的手光光地握着铁把,他谁也不看。这时阮
钰从外面回来,她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走了进去。老阮盯着自己的手看了一
下,突然他盯了他老婆一眼,他老婆胆小怕事,只顾低着头千手上的活。接着老
阮就站起身,他踢踢盘在脚边的一堆绳子,然后背着手走进屋。
总之这是一个让人不解的场面,我不知道老阮走进去意味着什么,心海镇上
关于老阮的议论既隐秘又公开,流传至今。
阮钰穿着一条裤腿宽大的蓝色裤子,走起路来像一条长裙,有点类似于二十
多年后流行的裙裤,她上身是一件白色的衬衣,当时镇上的女孩子穿白衬衣的不
多,白衬衣是在阮钰死了以后才大量流行的,她还背着一个军用挎包。阮钰的塑
料凉鞋踩在街面的沙子上发出干硬的喀嚓声,像割稻子时布满齿沟的镰刀一下一
下割在稻茎上的声音,蓝色的裤摆一前一后地拂着她的脚面,瘦削匀称的小腿在
宽大的裤口处时隐时现,裤腿的两摆婀娜多姿地流动,充满节奏和韵律,很像一
种难以言说的舞蹈。
阮钰的白色塑料凉鞋在沙面上富有弹性地跃起落下,鞋面的一颗黑色扣子闪
闪发光。我站在骑楼底下看阮钰的脚,它们走上台阶,从门口盛着防火沙的大水
缸旁边走过,粉红色的脚拇趾从白凉鞋的张口处露出来,像乳白色花瓣中的粉红
蕊芯。
老阮的手背布满青筋,像伏着一只硕大的蜘蛛,他的手掌长年被粗糙坚硬的
黄麻所磨擦,手上的皮翻起来,像齿尖一样坚硬锐利。老阮像老鼠一样轻盈地爬
上了阁楼他站在一堆黄麻中间,黄麻的气味充塞着整个房间,又闷又呛人,老阮
一连串地咳嗽不止,黄麻的气味从他身上一圈地震荡扩散。阮钰从一开始就没能
挣脱这种积郁已久的气味。据心海镇上流传的闲话说,老阮的阁楼上常常有一些
含义不明的可疑声音,自从阮钰十六岁来到心海镇老阮家,这种声音就开始存在
了。
心海镇的隔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木板,一类是墙脚下长了硝土的砖墙。两
种墙都有一些缝隙和墙洞,充满着大大小小的眼睛,因此心海镇上的传说都很准
确,精确到细节。有一次老阮的脑门被一种暗设的机关撞了一个凸包,早在他出
门坐到绞绳机跟前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有几个闲人已经拖着木板鞋等待在门口
观看。
听说老阮会催眠术,而且就是凭借这个本事撬到了漂亮老婆,并且让这个高
傲的才女变成自己胯下唯命是从的软弱小女人的。
又听说阮钰并不是老阮的亲外甥女。
在我的想象中,阮钰白色的肌肤在心海镇的阁楼里发出月亮的宿白的微光,
她单腿直立,另一条腿扬起,超过腰的高度,同侧的很托着膝盖的上方,另一只
手撑着桌子。门窗紧闭。阮钰穿着短命卷的修长洁白的腿泛出微湿的亮光,就像
水井里的月亮隐隐浮动亮她的四肢在黑暗中组成一只白色仙鹤的图案,显得惊奇、
不安,随时受到入侵的威胁。四肢打开,是一种不受保护的姿势,毫无防范的姿
势。
阮钰跟那个老阮到底有什么事呢?被打为ZB主义糟粕的催眠术到底是否存
在呢?这是我很难想象的,直到现在还是不断地有一些我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在
发生,包括我自己干的事。其实我早就应该明白,人是不可思议的,只要有能够
想出来的事情都是已经发生过了或者正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阮钰是我童年时代
的一道深邃的印痕,她修长的四肢和粉红色的脚趾像一种难以到达的奇异花朵在
心海镇幽暗的背景下缓慢地漂浮。
心海镇文艺队常常在农业局的一间大厅里排练,那时农业局的干部已经下放
了不少,开大会就不用在大厅里了,因此椅子都靠在边上,中间空出一大块地方。
心海镇文艺队有排练的地方,但经常漏雨,下着毛毛小雨的时候,瓦被雨水所渗
透,但雨水滴不下来。若是下着中等的雨,头顶上就会滴下雨来,滴到脖子里,
冰凉冰凉的,雨再下得大一些,排练场的地上就会形成水渍,东一块西一块,使
水泥地面看起来像一块被鸡弄乱的菜地。
专抓样板戏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叫郭正义,原来是农业局的干事,「文革」一
来就成了「红色风暴」的司令,生性爱看戏,当了副主任之后喜欢跟人夸口说:
我们县有个阮钰,他们有吗?地区文工团来调过阮钰几次,郭正义死活不放,阮
钰最后就没去成。
郭正义让心海镇文艺队到农业局的空大厅里排练,他住在农业局的宿舍里,
可以就近经常去看。郭正义喜欢把自己的事干得很漂亮,因此阮钰们便常常在夜
间排练到两三点,那时候因为革命,白天和黑夜经常不分,一百瓦的大灯泡悬在
屋顶,橙黄色的亮光从瓦缝里透出来,从外面看黑灰色的屋顶浮着一层光,显得
总之农业局的院子使我感到不安,哪怕在白天,我走进院子有点怪诞。
看到那些紧紧挤着的石榴树、栀子花树和芭蕉树,就不由得感到迷乱,生怕
自己会闷在这些密不透风的树丛里回不了家。院子里还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特
殊的气味,我一直弄不清这是从哪里发出的气味,从树上或是从空屋。栀子花白
得很愣地在绿黑的树丛里隐隐发光,让人觉得有一张人脸就在那里。或者突然一
阵风吹,满院子的树摇晃起来,真像藏匿着无数鬼魂,似乎一走动就会撞倒一个。
排练大厅有音乐响起,「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温馨和暖,另有一番
热闹的气氛。从窗口可以看见郭正义在指手画脚,有人在压腿、在定音、在说笑,
但如果大厅里有阮钰,这一切就会显得黯淡,显得缺乏应有的热闹,她那身素白
的戏装把大厅里的一切都冲淡了。她全身素白,无论站着还是坐着,走动或是不
动,这身不谐调的白色都格外触目,很是跳眼。
除了彩排,其他演员一般都不着装,只有阮钰例外,戏装一做好郭正义就让
阮钰赶紧试穿,阮钰正是那种天生适合素衣的女人,一套白毛女的服装穿起来,
立即就行云流水,人格外挺拔高挑,四肢修长,身体柔软,头发耀眼地黑亮,连
牙齿都瞬时具有了珍珠的光泽。郭正义将阮钰看了又看,每次排练就总是叫阮钰
把戏装换上,说这样容易进入角色,演喜儿的演员在旁边看着不吭声。
上半场没有阮钰的戏,阮钰穿着白毛女的一身白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轻飘
飘地出没在芭蕉树和栀子花树丛中,宽大的衣袖自在幽暗的树丛中雪白地一闪一
闪,她有时停下来,把一条腿抬到腰的高度,单腿站着不动。
直到郭正义从窗口探出头来喊:「阮钰!」
有时郭正义不喊,早早就走到院子里找阮钰,他转到树丛里,然后两人都不
见了。
大厅里还在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黑色的树丛里,栀子花时隐时现。
忽然有一天,阮钰的舅舅用他自己绞的黄麻绳上吊死了。
那天一大早就像着了火,人声乱乱地挤在老阮的门口,有人问:舌头伸出来
没有?
像雾一样的细雨在街肚里浮着,把清晨弄得像傍晚一样昏暗。
一阵一阵的女人哭声,像叹气一样。聚在门口的人们听到这叹气似的哭声就
自动静场,仔细辨别这哭声,互相用目光探寻,心里想:是不是阮钰?
阮钰那天晚上没住在阁楼里,她开始演戏之后就常常不回去了。阮钰走进老
阮家的样子就让人觉得她走进去马上就会走出来。她两片宽大的裤摆互相拍打着
发出风的响声,很冷傲很风采地从街头走到街尾的农业局,整条心海镇的女人都
隐隐感到阮钰或迟或早会成为她舅舅家的灾星,因此上吊的事情一发生,不少女
人暗暗松了一口气,好像总算没有白白担心,好像是一种期待,盼望已久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她们不知道在她们的心底深处是那么地希望阮钰倒霉,她们对老阮
有兴趣只是因为他是阮钰的舅,因为他是她们猜测中暧昧关系的一个因素,他是
一层水果皮,果肉在下面,果皮是不好吃的,但肉好吃,果肉就是阮钰。
何况他还可能会催眠术。
奴役人心的催眠术!
整整一上午,阮钰始终没有出现,使得老阮上吊的事情蒙上了层神秘色彩。
直到老阮的棺材抬走,人们还在门口站了一会,大家开始怀疑老阮的死肯定跟阮
钰有关。是不是阮钰害死老阮的?阮钰为什么对老阮恨之入骨?
再次看到阮钰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有人惊恐地发现阮钰披的白发格外地长,
全身白得近乎透明,在快速的追光下轻得像是没有任何分量,惨白的闪电凝聚在
阮钰的脸上,让人悚然心惊,不可避免地想到一个吓人的字:鬼。怀着这样独特
的目光去看阮钰的人肯定是郭正义,他坐在第五排听见阮钰用嘶哑得快要断气的
嗓子喊道:「我是山上的大树——」阮钰的歌声像一阵一阵的寒气直逼全场的每
一个角落,我觉得老阮的眼睛正从礼堂的天窗向下凝望,恰如一团飘忽的鬼火。
阮钰演到最后终于唱不出声音了,到最后是翻身农民合唱太阳出来了,嗬哈
依哎哟,阮钰白色的长发编成整齐的大辫子,穿上红花上衣接过枪加入革命队伍
朝太阳的方向走去。很多人看到阮钰眼睛里闪着亮晶晶的泪水,非常符合剧中人
物「激动」的要求。只是她的嘴巴一张一合空洞无声,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就会
认识到阮钰的泪水代表了另一种意义。
这是阮钰的最后一次演出。
当晚郭正义宣布文艺队全队休整一个星期,上午练功,下午学习太祖同志的
讲话,晚上自由活动,等阮钰的嗓子恢复过来再排练演出。郭正义拍拍阮钰的肩
膀,说:我送你回去。
阮钰以往演完戏常常住在农业局那间大厅旁边的空屋子里,里面有两张床,
是农业局的临时招待房,这次阮钰仍然回农业局。
据郭正义后来说,阮钰一路上一言不发,情绪不好,他送她到招待房门口就
转身回家了,准备让她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来看她。
但是阮钰没有明天了。
第二天一大早到树丛里做甩手操的烧开水老头看见沼气池的水面上浮着一只
白色的塑料凉鞋,沼气池的边上的浮土也被踩了几个很深的新脚印。白凉鞋是阮
钰的,阮钰被捞上来的时候另一只凉鞋还穿在她的脚上,她全身被水泡得像石灰
一样白,白得跟她的塑料凉鞋同一个颜色。
郭正义认为阮钰是半夜上厕所时路过沼气池不慎掉下去淹死的,这种说法使
很多人不能接受,因为上厕所并不一定要路过沼气池。也就是说,除非阮钰到树
丛里晃荡才有可能掉进沼气池,但阮钰比任何一个人都更熟悉这里的地形,这个
挖好以后一直未使用的沼气池有多深她不会不知道,雨水积在池子里亮晃晃一片,
即使在没有月亮的夜里也看得见。
但阮钰为什么半夜三更逛到树林里呢?
没有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阮钰就像一个古怪的谜一样从心海镇消失了,她的死使郭正义受到了打击,
他从此不再过问文艺宣传队的事情。
以上的事情大半是心海镇上的传说,所以才那么零乱不堪没有逻辑,现在我
要叙说一个我亲眼看到的场面。
我在心海镇居住的时间是我八岁到十一岁,正是阮钰从走红到死的三年。有
一天中午我到农业局的院子玩。那是个大太阳的中午,是夏天,非常闷热,蝉声
响得铺天盖地气势汹汹,院子里很静,房屋和树木白晃晃地闪着金属的光泽,没
有一个人。我有些害怕,不敢独自钻进树丛里,尽管那里有一种我非常想要的硬
壳虫,我打算把它们养在火柴盒里。
我走到大厅与招待房相交接的地方躲太阳,大厅的窗口大开,我冲里面看了
一眼,没有人,几把椅子歪歪扭扭地放看。招待房的窗子紧闭着,玻璃上贴着旧
报纸,屋子里面好像有动静,但是没有说话的声音。我好奇地想知道屋子里正在
干什么,我使劲地在糊玻璃的报纸上找洞眼,果然在右下角的地方发现了一个用
烟头烫出来的小孔,这孔眼非常小,主人在把报纸糊上去的时候大概没注意到。
我趴在玻璃上透过这孔眼往里看,看到了一个使我非常吃惊的场面。
阮钰全身赤裸地站在屋子中间,她单腿直立,另一条腿扬起,超过腰的高度,
同侧的手抚着膝盖上方,这是一个练功的姿势,阮钰在树林里常常这样站着,如
果把托着膝盖的手拿开,举到扬起的腿平行的位置,就是舞台上常见的姿势。
阮钰脸朝窗,低着头,她赤裸的正面正好对着我,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逼近的
裸体女人,这使我感到窒息,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天窗把一束正午的阳光从阮
钰的头顶强烈地倾洒下来,把她全身照成半透明,身上的汗毛被阳光照成一道金
色的弧线,一种逼人的赤裸裸的美。阮钰的裸体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摧毁了我对别
的女人包括我自己的身体的欣赏,我相信我此生再也不可能看到如此精美绝伦的
裸体。
墙角有什么动了一下,我看出那是一个人,郭正义,他穿着衣服坐在角落的
板凳上。
我永远都忘不了那时阮钰梦魇般的呢喃。
「是的。」
「是的。我爱演戏。」
「是的。我的人生都是排好的一场戏。」
「是的……」
催眠术!是催眠术!
郭正义也会催眠术?抑或和老阮是一伙的?
我想跑!我想把这天大的秘密公之于众!
猛回头,却迎面撞上了一张苍老的脸。
老阮!
「哎哟哟,幸亏我回来看一看啊。」
我不能动。
确切地说,是不想动。不知道为什么。
任凭他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当时尚显稚嫩的脸庞。
「阮钰很漂亮,有拿来当性奴的资本……但不漂亮的呢?你说,萍萍,像你
这样不漂亮的女人,应该怎么处理呢?」
他桀桀地笑着。
「那当然是读书啊。腹有诗书气自华嘛。三十岁之后,气质才学都有了又带
了点名气之后,啧啧啧。」
「听着,萍萍。」
「你要努力学习。」
「你要热爱文学。」
「你要成为作家。」
「然后,你要回来,侍奉主人们。」
是的,我想起来了,所以我才会成为混沌国首屈一指的才女,女性主义文学
的代表的作家。
所以我现在才会以记者的身份回归,赤裸着跪倒在比当年更显年迈的郭正义
身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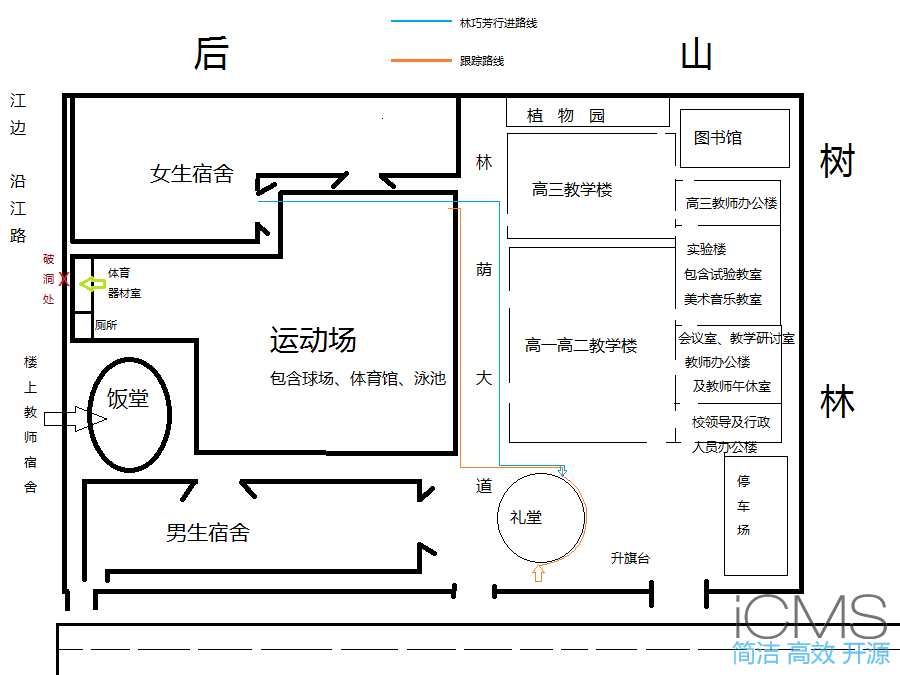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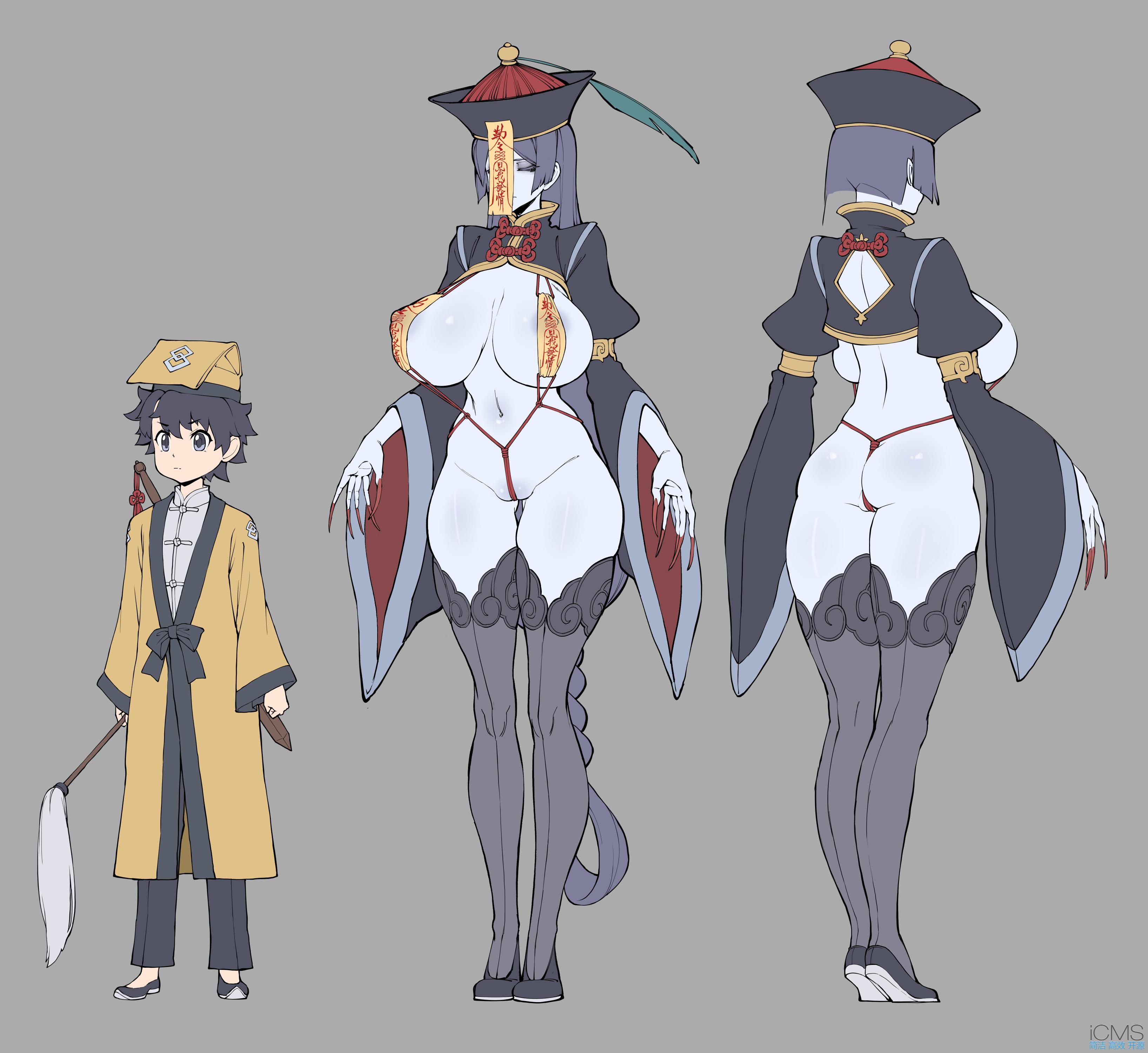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